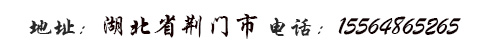仙人掌的话海派
|
白癜风初期什么样的 https://m-mip.39.net/czk/mipso_7388212.html??温馨提醒:《仙人掌的话》不写任何评价性的文字,更不可能有任何涉及地域歧视的观点,所有的故事都关乎我自己。我相信没有一种文化,优于其他文化。但申城是我的家乡,所以她是我心中的第一名。理性阅读,尊重自己。在上海的十八年里,我从未意识到腔调文化对我影响如此之深。离开黄浦江求学,我才发现腔调已经成为接人待物之根,评人论事之本。最近的推送连续着更新我自己的故事,反倒是已经很久都没有再写过正经一些的话题了。每个城市有它自己的风格,里面走出来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小小的飞机驮着我来到遥远的岭南求学,作为一个异乡人反而把家乡看得更清晰真实。广东人的低调务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们把不同的文化送进这座校园,有的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广东的烟火气,让我想来说说我的家乡,这座以“魔力”闻名,点缀在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宝珠,究竟以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养育着我。其实在广东求学这将近一年的时间,身份认同是我最难取得的东西。虽然大多数时间我都感觉还不错,可我刚入学时确实很少告诉别人我来自哪里。后来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很快乐,stereotype这种东西不是我一个人能消除的。有的人说上海人精明狡猾,有的人说上海人矫情自大,有的人说上海人是“既得利益者”,有的人说上海在吃全国的红利。有时朋友们在聊一些他们才懂的事情,我总是很难插上嘴,而我懂的一些事情,他们却又不能理解。这周的《文学话语研读》课上,Stephen要我们讨论《Dracula》中的一段情节。一开始我完全看不懂这段到底在说什么,后来却深以为然。剧情大意是这样的:叙述者角度:Mina(女性,其友人Lucy牺牲)Mina看着几个男性同伴商量着接下来的行动,出于“绅士礼节”,他们认为唯一的女性Mina应该安全地睡觉,所有危险的行为应该由男人们完成。Mina觉得自己的友人刚刚死去,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能睡得着,她觉得这种“绅士礼节”只是想把自己排除在这个行动计划之外。但Mina不敢提出反对,因为她害怕反对之后其他人会干脆全盘将她排除在外。这段里的一句台词我印象很深,范海辛教授在提意见时用的是“vote”,但其实从前后文来看,他坚定地认为只有这种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Mina的心态是小组讨论时我常有的状态。我很难一一去反驳那些我不喜欢的错误的强加在我和我的同伴们身上的标签,因为他们说的话其实对又不对。他们口中的“上海人”并不是东海明珠的特产,他们说的这些事全国各处都在发生。开始的时候,我和以前的朋友们说,我真的好后悔出来读书。如今我想说,我好像已经不在意这些了。腔调文化是一种很奢侈的文化,这是我来到广东后明白的道理。一个事实是,上海小囡爸爸眼中最大的“不孝”是嫁了一个外地男孩。这也是很多时候被批评排外的一个扳手。不过其实我们的家长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外地”这两个字,也不是在意房子车子这些物质的东西。上海人把金钱与物质每天挂在嘴边,其实是羞于因为心里藏着的那些东西讲出来。上海的父母,总是非常爱孩子、爱家人。家庭不是上海人的一切,但家庭的优先度非常高。无论是儿子娶媳妇还是女儿嫁老公(或者其他情况),父母总是极度担心对方会欺负自己的孩子。如果说父母常情皆如此,那么上海的爸爸妈妈估计是爱孩子爱到把除了自己孩子以外的所有小孩都事先做好了有罪推定。从来不是地域的问题,只是上海人把感情与道德看作是第一要素。这就是腔调文化的精髓与基本所在。出来读书后我才明白,上海人是真的非常奢侈地赋予一些虚无的东西一票否决权。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我至今都搞不明白要如何解释这一矛盾。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我们和深圳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样追求经济至上。可是奇怪就奇怪在,物质至上的上海人总是追求虚无的东西,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腔调文化是一种规则文化,它不是食物、建筑或者习俗方面的文化,它是对人的一种要求,一种评价人的方式。它要求人在做事的过程中注重手段方法过程是否讲道德、是否高尚,至于事情的结果,倒是交给了天意。来粤后我每每和家里人通电话讲些事情,妈妈总是跟我说有的底线不好碰的。其实上海人心里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唯独就是在做人做事的方法上,我们总是希望更好一点,更高尚一点。这种对道德的追求深深刻进血液。上海人说的脏话有一大半是批评别人不够聪明,这种“聪明”其实指的就是: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做事情呢?无论你追求的目标是物质还是精神,是低俗还是高贵,你不能冲着这个结果去做事情,那太有失水准。你去漂倡不要紧,但你不好白漂。所以如果你走在市中心的一条条小路,你经常会遇到一些打扮得老有所姿的老太太拎着皮包走进一栋摇摇欲坠的电线水管排得乱七八糟的危楼民房。“要点面孔”,“讲点道德”是吵架的时候讲的最多的话。其实也是腔调文化的要求,上海人虽然极度嘴碎和挑剔,却从不因自己嘴巴里说出来的那些理由否定一个人。肮脏恶毒的评价只是化吐槽与期待于一身,真正的厌恶是端庄的沉默。对人不对事,我们相信这样才公平。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为了一件做错的事情受到惩罚,一个卑劣的人不应因为一件做好的事情受到褒扬,因为事情哪里有人重要,事情都可以被复刻,人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上海的官方城市文化叫“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宣传语是“和衷共济,四海一家”。我们欢迎所有有梦想的人,不是有能力的人,因为上海有太多有能力的人,我们要的是有梦想的人,真正爱着这座城市,爱着自己人生的人。最后想讲的是,上海人的情感是矫情而复杂的,正如每年黄梅雨季的天空。上海人的心里把所有的爱与憎全部糅合在一起,没有绝对的爱,也没有绝对的恨。上海人没有一直坚持着的东西,精明狡猾就在于这里,但上海人总有一根魂藏在行为处事的暗处,人本的思想总是随处可见。所以请大家阅读一篇路明老师的作品,把上海人情感里的复杂写到了极致。上海来的外婆路明 那时外婆还不老。她时常倒几次车,来小镇看我和我妈。我很少去汽车站接她,她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亲热地叫我“囡囡”。 我很开心,外婆从不空手来。旅行包里装的,是外婆厂里做的鸡蛋糕、苔条酥和苏打饼干。酒心巧克力一般日子是吃不到的,除非我生病了,或者是我和我妈的生日。还有方便面,那时叫“梭子面”,是高档的食品,我捧在手上干啃,又脆又香。 我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短发清爽,眼睛明亮,面颊有两朵红晕。外婆喜欢唱沪剧,唱越剧,唱黄梅戏,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后来说不让唱,她就不唱了。外婆能写会算,又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很快被委以重任。八十年代,外婆负责厂里的外调工作,碰到去安亭、黄渡那个方向,她就早早办完事,花一角六分买张长途车票,跳上开往小镇的班车。 外婆通常在下午抵达。我妈说,姆妈你坐,我去弄碗面吃。外婆摆手,说静芝你别忙,我吃过了。据外婆说,汽车站下来有一家饮食店,小馄饨做得好吃,每次她来都要点一碗。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外婆是真的喜欢吃小馄饨。 镇上有两家国营招待所,外婆嫌不卫生,住在家里又添麻烦,往往没说几句话,就急着赶末班车回上海。我妈领着我送外婆,往她旅行包里塞几个咸鸭蛋,有时是一段青鱼干。一角六分坐到安亭,三毛钱乘“北安线”到陆家宅,再换40路电车回家。 来过几次后,外婆的小镇方言就说得有模有样,比我妈地道多了。她笑着跟我们的邻居打招呼,临别时再送上一把大白兔,拜托他们多多照顾我。邻居们都说,这个上海老太太真好,和气。我对外婆的社交不以为然——外婆就说我妈笨,不懂人情世故。 更多的时候,我跟我妈去院部打电话。医院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装在院长办公室外边。电话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接线阿姨去楼下扯一嗓子,外婆再跑出来接。外婆在电话那头讲,囡囡乖吧。我说,乖的。外婆说,囡囡想吃啥。我说,酒心巧克力。外婆就笑了。 那时爸妈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我不愿听他们吵架,就选择离家出走。不会走远,在医院宿舍区范围内,找一个冷僻角落坐着,或者偷偷跑去院部打电话给外婆。 第二天,外婆来了。我爸还在学校上课,我妈和外婆先吵起来了。我妈说外婆“专制”“包办婚姻”,外婆说我妈没良心。每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她会觉得,这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外婆引起的。我妈十六岁那年,一腔热血地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外婆偷偷跑去她学校,把志愿改成安徽怀远,只求离上海近一点。大红喜报贴出来,我妈傻了眼。相约去黑龙江的同学说她是“叛徒”,我妈没法辩解,回家大哭一场。 在当了三年农民后,我妈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毕医院。外婆到处求人,给她张罗相亲对象,找到了在小镇教书的我爸。我妈对我爸很不满意,最后是外婆拍了板。外婆的想法很简单:嫁给我爸,我妈就能调到小镇工作,好歹离上海近些。 我妈指着外婆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认识“这只男人”。外婆说,不是我,你还有的苦。我妈说,苦就苦,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外婆说,你当时都快三十了,我不做主谁做主。我妈说,四十也跟你没关系,我可以不结婚的。外婆气得直哆嗦,转过头对我说,你妈这叫什么话。 外婆是抹着眼泪离开的。我妈赌气没送她,是我目送外婆挤上了末班车。外婆拎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床单和被套——她原本打算去招待所住一晚的。 第二天晚饭后,我妈拖我去院部。仿佛等了很久,听筒里传来外婆的声音——喂,喂,啥人啊?我妈攥紧话筒,手微微颤抖,不说一个字……喂,静芝啊,阿是静芝……啪一声,我妈挂掉电话,拉着我走了。不过最后我也想说,上海人命里的这道魂与坚持,实在太过奢侈。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nrenzhanga.com/xrzfz/7926.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周一茶8仙人掌茶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