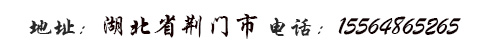张桂兰散文村口,那棵伫立的槐树
|
村口,那棵伫立的槐树河南邓州/张桂兰回家,总想去看看村口的那株槐树,看看我小时候住着的老屋。老屋里住着父母和孩子们,是兄弟姐妹们长大的地方。住过的老屋,原来是三间堂屋,后来靠西山墙又搭建了一间矮一些的小屋,共四间房子,俱是黄土夯实的土墙,土墙青瓦,瓦有些老旧,墙有些裂缝儿。西厢是一间小灶火,东边是小菜园儿。菜地用树枝扎成篱笆围着,有的地方还长着仙人掌。仙人掌开花很漂亮,果实成熟后是紫红色的。曾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吃过仙人掌的果实,甜中微酸,好吃的味道至今还藏在心中。后来小菜园没了,仙人掌也没了,用黄土夯了院墙,围了个大院子。院里打了手压井,井边开了个小小的水池流污水,水池里种了几段莲藕。院子南墙边长了两棵香椿树,每年春天会采香椿芽叶吃。再后来,填了小水池,东厢也盖了一间小灶火。如今,老屋没有了,只余一节节断墙,那一次来看还是满院的枯草,这次来看邻居开荒种了青菜,开辟的菜园生机勃勃。西厢灶火前的柿子树依然挺立,两棵香椿树也粗壮不少。一晃神,好象妈妈还在门前坐着,右手的缝衣针习惯性地在头发上篦了篦,低头缝补着衣服。脸上蕴着温柔的笑意,鼻音里低唱着优美的歌。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美好的情绪中。我蹲在母亲身旁,仰看着平生仅见的母亲的柔美和与柔美连在一起的好心情,心里柔软的象一根面条。夕阳夕下,橘红的晚霞笼罩着院子,笼罩在母亲身上,把一切都镀上了金光。我家村子四面是高高的寨墙,南北西三面的寨墙外是人工寨河,东边自北向南是湍河流过。这是老辈们早年为防匪患保护亲人而建筑的巨大工程。当时寨内应该有炮楼瞭望塔什么的吧,但我没见过。记事起,寨墙只有一人多高,寨墙顶上走人,两边零星种些树,寨河沟里有时还种着禾草庄稼什么的。寨墙顶上路的两边长着茅草和巴地草。小时候爱挖茅草根,象甘蔗样一节一节的细细的白色茅草根,一嚼一口清甜,被孩子们当零食吃。巴地草孩子们串音叫它蚂蚁草。茅草巴地草爬在寨墙左右两边,保护着寨墙的土不被风雨冲刷的那么快。如今的寨墙己不成为了墙,成了三面环围着村子的长长的土堆,且每年以看不见的速度降低着高度。东面靠河的寨墙也早己随着河岸的坍塌而不见了踪影。寨门也早就没了门,是一种敞开的路而己,习惯上还是叫它们为“门”。我家在村西北角,下地干活一般走北门和西门,出门赶集则走西门。西门出去是乡所在地的集镇,通往县城,然后更远。哥哥姐姐们回家是走西门,离开也走西门。西门的寨墙上,长着一棵槐树,春天开花,夏天遮荫,冬天树叶落了,肃穆地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迎来月落日升。哥哥在远方工作,回家探亲,然后又走了,妈妈送哥哥到西门,站着看他走远,哥哥一边往前走,妈妈一边向寨墙上移,最后一直挪移到最高处的槐树下,手扶着槐树,眼晴随着哥哥的身影移动,哥哥的身影成了个小黑点,妈妈依靠在槐树上望着那小黑点的方向,久久回不过神来。姐姐出嫁了,婆家近,不象哥哥出门那么远,但每次回家,妈妈也相送,有时送出家门,有时送出西门,随着妈妈的年迈,妈妈站在村头槐树下的时间也越长。一天,我也出远门了,中间回家,妈妈很是激动,那次离开,妈妈也是陪送,陪着我走到西门,看着我走远,慢慢从路口又挪到寨墙高处的槐树下,怔怔看着我远去。我背着母亲的牵挂,回头看来,妈妈手扶槐树,一眼不眨。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来,朝妈妈挥了挥手,让她回去,妈妈依靠在槐树上,手搭凉棚眯着双眼看着我走的方向。走到邻村近旁,往前走村庄就会挡住了视线,再回头看向村口,妈妈和槐树融为一体,不知道妈妈是槐树,还是槐树是妈妈。走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穿过了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妈妈的视线一直跟在脑后,妈妈的牵挂和祝福一直植在心田。从青年,到中年,一直到现在的跨近老年,每当想起妈妈,总感觉妈妈还站在村口的槐树下,牵肠挂肚地瞅着她的孩子们,一个个地离开她的身边,走向人生的圆满。如今,母亲早己故去,只留下敞开的村路,和村口那棵伫立的槐树。﹌﹌﹌﹌﹌﹌﹌﹌﹌﹌﹌﹌﹌﹌﹌﹌﹌﹌﹌﹌﹌﹌﹌﹌邓州文艺 喜欢作者请给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nrenzhanga.com/xrzfz/9369.html
- 上一篇文章: 回家丨李娟侠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