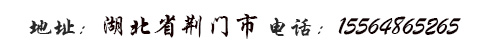棉布裙一朵仙人掌上花
|
年,我错过了最有价值的电影,《掬水月在手》(所在的小城太小了,居然都没有排片);却读到了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掬水月在手》。 它是电影的同名书,可以说,这是关于叶嘉莹先生最完整也最忠实的记录,够厚重,亦够精彩。 《掬水月在手》,不仅题目隽永有深意,它的结构篇章,也颇费了一番思量。其每一章的篇名,皆为叶嘉莹的诗句。 既有纵向的时间轴,又有横向的空间线,既有叶嘉莹的自述,亦有亲朋好友同事学生的他述,它们纵横交错地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鲜活充满了词风古韵的叶嘉莹。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其祖上是旗人,本姓叶赫那拉,曾祖父是咸丰同治时期的二品武官,祖父是光绪年间进士,他们祖宅的大门上曾有黑底金字的横匾:进士第。 小时候,他们一大家人住在北京察院胡同的四合院里。在叶嘉莹的记忆里,这座宁静的庭院由内而外蕴含着一种中国诗词的美好意境。 “家里永远很安静,可以听得见蝉鸣和蟋蟀叫,再有就是人的读书声了……旧时家里古典诗词的氛围确实对我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我的知识生命和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的……” 尽管身在书香之家,却生逢乱世。从军阀混战,到七七事变,叶嘉莹自小便看多了尘世的苦难,15岁时即写成《咏莲》一首:“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是家学的渊源,是个人的秉性,是内在的坚持,是外界的逼仄,让叶嘉莹成为了叶嘉莹。 年,17岁的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也是在这一年,她的母亲病逝。这是她第一次经历死生的打击。“自母弃养去,忽忽春秋易。出户如有遗,入户如有觅。”(叶嘉莹《咏怀》)。 当此时,叶嘉莹的父亲正随着国民政府步步撤退,连叶母已经去世都不知道。 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年,她与赵钟荪先生结婚。当年11月,叶嘉莹随先生撤退到了台湾。 年,她的丈夫赵钟荪先生因为“白色恐怖”而被捕入狱,直到年才出狱。三年时间里,叶嘉莹一个人带着孩子独立支撑,走过了一段相当凄苦的岁月。 经历过忧患,叶嘉莹对于诗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她从诗里读出了人生,读出了家国,读出了盛衰成败。 台湾作家白先勇是叶嘉莹的学生,他说,是叶先生引导他进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殿堂。“她一口北京话,纯正而富有教养,念诗的声音很迷人……我觉得她本人简直是把那种盛唐的精神带到课堂上来了……” 在台大,叶嘉莹总是身着旗袍,气韵优雅,举动风华。她意暖而神寒的气质,令一众师生倾倒。 台湾诗人痖弦,将其称为“穿裙子的士”,真是最恰当不过! “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晴明半日寒乃劲,灯火深宵夜有情。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 这是叶嘉莹19岁时写成的诗。才19岁的叶嘉莹对于出世入世已经有了颇为成熟的想法:不需要隐居到深山老林里去追求清高,我可以身处尘世之中做我要做的事情,内心却要永远保持一片清明。 叶嘉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从年登上大学讲台,她就一直活跃在教坛之上,直至今天的耄耋之年。 如今,她定居在南开大学的迦陵学舍,学舍的月亮门两边的对联,仍旧是这两句诗:“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它真正表达出了叶嘉莹立身处世的理念。 年,叶嘉莹前往哈佛大学,和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台湾,她一直都没有离开诗词、离开教坛。 在朋友们眼里,她就像中国文化的一潺清溪,缓缓地浸润了每一块热爱文化的土地。 少年即成名、现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田晓菲教授和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邝龑子对叶嘉莹都非常钦佩,说她是大家规模,学者典范。 在台大讲课时,课堂向来是场场爆满,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听课的学生。在海外讲课,她亦是一气呵成,三个小时不坐下来也不喝水,出口成章,风采照人,令人感动,亦令人向往。 “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 年,叶嘉莹去往加拿大的温哥华教书。年,中国和加拿大建交,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探亲,她激动兴奋,写了一首长长的《祖国行》,中有句云:“银翼穿行忆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 其时,叶嘉莹的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她想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她以后可以享受余年。却不料在年,叶嘉莹的长女言言和女婿出了车祸,两个人双双罹难。 这于叶嘉莹简直是晴天霹雳:“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巨大的打击让叶嘉莹对于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一定要从我的小家里跳出来。我要回国,我要回去教书,我要把我的余年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 淡江大学的施淑教授说,叶嘉莹用诗词溶解生命的伤痛; 加拿大的文学博士陈山木说,魏晋风骨就是叶嘉莹的风骨; 她的学生施淑仪说,叶嘉莹先生无论经历怎样的凄风苦雨,始终都是“独陪明月看荷花”“万古贞魂倚暮霞”,她总有一种坚强的信念和持守在,所以她总能超越人生的种种障碍,绽放出灿烂的光彩。 “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桑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年,叶嘉莹申请回国教书。“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背井离乡四十多年,她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诗词教学。 先是北大,后是南开。从受到某些人的质疑,到举座皆惊、备受推崇。叶嘉莹,终于成为了今天的叶嘉莹。 在南开大学,每当有叶嘉莹先生的课,大家都会闻风而至。几百人的教室,座位上、阶梯上、窗台上、窗外边,都挤满了人。 南开大学中文系为了保障自己的学生能够听课,就刻了章做了听课证,结果外面想进来的人就自己刻印做证,照样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白天的课排满了,但学生的热情不减,学校只好把课排到了晚上。正是“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如今,已近期颐的叶嘉莹,依旧神采奕奕地活跃在教坛之上。她说,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我要把这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读完此篇,仍旧不忍释卷。我勾勾画画,翻了再翻,尤喜叶嘉莹的《纪梦》一首: “峭壁千帆傍水涯,空堂阒寂见群葩。不须浇灌偏能活,一朵仙人掌上花。” 叶嘉莹先生,就是一朵仙人掌上花。她一生坎坷,却独得了诗词的雨露。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依旧绽放出了美丽的花朵! 棉布裙以教书为幸,以写字为荣。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nrenzhanga.com/xrzzw/7581.html
- 上一篇文章: 仙人掌喜剧X西湖之声引爆杭州脱口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