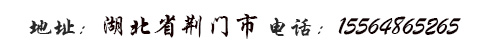关注钢铁行业烟气治理向何处去中国绿发
|
年是我国蓝天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蓝天保卫战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客观的问题,比如停限产措施越用越频,比如南方江浙沪优良天数明显减少等等。在持续的跟踪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雾霾治理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对于其成因,大家也有了一些新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的意见与看法,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相比于一味的歌功颂德,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虽然北京的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但低污染、轻污染天数却一直在持续增加,就是PM2.5数值在50-之间的天气,几乎成为常态化的存在。这是北京的实际情况。 我们从年开始对北京周边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雾霾情况进行了实时监控。我们得到的监控数据显示,北京雾霾天在减少,但其他城市在增加,比如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地的雾霾天数增加就很明显。保卫北京实际上是以部分牺牲周边的工业生产为代价的。随着国家停产限产力度的加大,之前只要工厂做了超低排放,就视同排放达标,该工厂可以不停产、限产。但从年开始,无论工厂排放数据指标怎么样,只要属于重工业企业,就得按“天气预报”的需要来安排停限产。当然,目前各地已经在做环境绩效评级的事,A级企业可以不用停限产,这是好事,但如果各地大部分企业都达到A级后,雾霾还是频繁发生,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北京空气质量确实有改善,但是统计标准目前并没有跟国际接轨,比如我们现在是以50μg/m3作为判断PM2.5的空气优良质量等级红线,而欧美等国家的标准是15μg/m3,如果以15μg/m3为标准,我们现在的雾霾治理还任重道远。对于年2月疫情状况下北京雾霾及12月哈尔滨发生的持续性严重雾霾,普通老百姓产生了很多的不理解。一个现实问题是:一停限产雾霾就减轻或不发生了,但工厂一开雾霾可能过不了几天就又来了,这在河北地区特别明显,而老百姓要问的是:不是各个工厂都达到超净排放标准了吗?有些工厂门口贴着大大的“我们排放出的烟气比空气更干净”等标语,为什么烟气都治理这么干净了,还会有雾霾发生呢?普通老百姓不理解,一部分科研工作者内心也有同样的疑问:我们的大气治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几年我们通过收集来的大量数据及走访调研发现,在现实中存在的以下三个问题,可能是在当前超净减排趋势下,雾霾依旧低浓度、高频率发生的原因。 第一是氨气溶胶的问题。 在硫、硝、尘三项指标都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雾霾的消除还得靠停限产措施,这是否说明我们仅控制这三个指标是不正确的做法?美国和欧洲一些学者及清华大学几个研究团队对北京、上海大气质量研究结果显示,这两个地区空气里面的成分氨气溶胶占到40%左右,北京地区有时段甚至超过45%。但氨气溶胶污染目前还不在我们的控制指标内。我们现在烟气脱硫脱硝需要大量地喷氨水。从年开始要求电厂脱硝,到年国有大型规模以上电厂全部完成脱硝任务,从年开始要求钢厂脱硫脱硝一体化,从这个时候工业企业开始大量地喷氨,空气里面的氨气溶胶明显增加。现在电厂、水泥厂都有关于氨气溶胶排放指标的监测,但是现在国家并没有把氨气溶胶排放列入到钢铁冶金行业的排放指标监测中。事实上,由于非电行业的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electiveCatalyticReduction,SCR)是布置在脱硝除尘之后,氨气溶胶无法被粉尘、脱硫剂吸附,其氨气溶胶逃逸现象非常严重,水泥、火电行业已经将氨气溶胶列入检测及控制指标,为什么钢铁冶金行业的排放标准里却至今没有列入? 类似氨气溶胶的问题是不是还有?比如有专家提出还存在SO3气溶胶问题,我们也在湿法脱硫监测时发现该现象确实存在,排放量具体有多少,还在检测过程中。这几个指标没有管控,造成了即便我们现在烟气看似很干净,但实际上因为指标宽度不够,还有许多致霾物质的存在,这些物质是不是造成“高频率、低浓度”雾霾天频发的原因? 第二是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 在我们环保领域,尤其是在大气治理领域,现在还是由主管部门规定用什么样的技术,还存在其他行业早就消失很久的“推荐技术目录”问题。创新就被这个目录给扼杀掉了。更让从业者从内心质疑的是,现在主管部门指定的所有技术全是国外引进的,国内原创技术一项也没有。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为什么几十年大气治理走到今天,我们在工业烟气治理上的发明专利不超千件,而口罩、净化器等产品领域的创新却动辄几万件、十几万件。从这个层面上讲,创新动力不足,可能是工业烟气治理始终走不出“一段晴,一段雨”怪圈的原因之一。 这两年,我们在跟企业接触过程中也发现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各方质疑。比如,主管部门所指定的技术路线里面有一个就是SCR技术。SCR技术是从欧洲引进到中国的,现在国内大概有几十家公司获得了技术授权,因为它需要通过大量喷氨才能达到超低排放指标,否则超低排放的指标就控制不下来,所以这个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氨逃逸,也就是说会产生大量的氨气溶胶并进入大气中。现在,在钢铁冶金行业,原来假设我们按1:1的比例反应,一吨的氨水可以反应一吨的氮氧化物。现在为了达到超低排放的指标,需要喷1.5-1.6吨左右的氨水,假设氨按1:1的比例反应掉了,那么还有0.5-0.6吨的氨就逃逸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雾霾里面的氨气溶胶占到40%这么高比例的原因。往深层次研究,是因为我们在脱硝脱硫技术方面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原创技术,所以只能引进国外技术。在引进国外技术基础上,主管部门把国外技术原来的技术极限指标,比如,mg/Nm3、mg/Nm3的氮氧化物指标,强制升到了35mg/Nm3。国外做技术的时候它一定是平衡的,它觉得喷一吨氨,那么控制指标到mg/Nm3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氨是成比例的,是能够被反应掉的,逃逸是可控的。但我们强行把这个指标提高到了35mg/Nm3,已经超出了国外引进技术的可控范围,因此就造成了过量喷氨,让这个指标检测时达标。由此可见,主管部门对指标不应该过度地追求低,而是应追求排放物质的平衡。我们不能说把氮氧化物控制下来了,硫控制下来了,但氨逃逸高了。大量的氨气溶胶进入大气中,成为雾霾产生的另外一个因素。 实际上,有几项污染物指标都存在这种情况。过度追求低指标,过度追求不恰当的数据,表面好看,实质增加了新的污染物排放。以氨气溶胶为例,在这么低的排放情况下,还会带来能耗的增加,带来物料消耗的增加。那么能耗增加、物料消耗增加,就使得物料变成固废的数量又增加了,固废处理现在又不在监控范围内,所以固废又形成了新的污染,又增加了新的环境负担。如此一来,环境治理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指标一开始下来了,看似漂亮了,但是其他污染物在增加,能耗在增加,碳排放在增加,整个环境的物质不平衡在加剧。 再比如说前几年很活跃的活性炭吸附技术,是主管部门力推的技术,年起由环保领域的相关领导出面开始在钢铁领域推广这项技术。在当时的环境下,主管部门的做法也没有错,只是认知不够。在当时的认知情况下,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觉得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活性炭技术是可循环的,它可以把空气里面的硫捕捉下来做硫酸,然后它就可以循环起来,看似很好。但实际上从年开始强推到年,已经是第4年了,从年开始基本没有企业采用活性炭技术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技术虽然在目录里排第一,但是在使用时,会发现控制35、50mg/Nm3等指标比较困难,而且活性炭解析过程会进一步消耗蒸气、水、电等资源,硫回收环节的作业环境也较差,周围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organic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nrenzhanga.com/xrzpz/11936.html
- 上一篇文章: 农发行忻州市分行组织员工开展消防演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